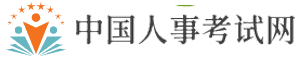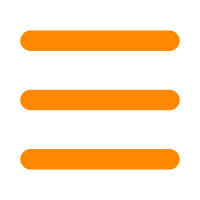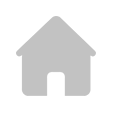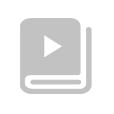不论是在经济迅速成长阶段,还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 20 年,日本政府一贯秉承了均衡性富民政策,不只维持了薪资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的较高比重,更通过多种再分配调节政策,进一步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大大降低了基尼系数,在收入分配中较好达成了兼顾公平与效率,使日本成为全球劳资关系好及社会安定和谐的代表性国度。但伴随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其过分偏向年长人群的年金及社会保障规范,不只使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更严重干扰了居民消费,制约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健康进步,有关经验教训均具较高的借鉴价值。
1、日本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情况与主要特点。
(一)劳动报酬率高,基尼系数低,收入分配相对公平。
日本的劳动报酬率相对较高,居OECD 国家前列。在与国内目前人均收入相对应的上世纪 60 年代,与沿海区域人均收入相对应的上世纪70 年代,在达成经济高速成长的同时,较好达成了工业化中后期的收入倍增计划。在此期间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 GDP 增速,劳动报酬率由 1960 年的 40%,提升至 1975年的 55%,之后一直维持在 50%以上。日本上世纪 60—70 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主如果打造在劳动生产率持续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这与日本政府和企业在技术研发、教育及培训等方面的持续大规模投入密不可分,政府在做好进步规划的同时,更重视对企业长远进步的人才、技术等要紧范围的支持,致使经济高速成长、劳动生产率提升与收入持续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与互动。同样,经济高成长期企业效益的迅速增加、用工需要和职员劳动素质的不断增强,则成为提升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比重的最好机会,日本政府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成功推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的收入分配相对公平,在上世纪 60—70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 0.3—0.35的黄金区间之内,90 年代后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 0.4 的警戒水平之下。在上世纪 60—70 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即便是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也一直维持在 0.4 之下,正是日本政府在工业化中后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得力政策,与企业终身雇佣制和职员以厂为家的集体精神,一同造就了日本制造和日本品质的神话,也形成了那个时期的日本,假如一个人收入较低,不是能力不足就是比较懒惰的鲜明年代烙印。经济高速成长期很多的政府财政盈余,致使日本政府有意愿和能力来更好地解决收入再平衡问题。
健全的社会保障规范体系更成为日本国民收入分配再调整的主要方法。伴随泡沫经济破灭前后,日本第一次分配基尼系数的提升,再分配的调整力度也随之加强。
2008 年的再分配调整改变度达到 29.3%,其中社会保障方面的改变度为 26.6%,税收调节方面的改变度为 3.7%。
(二)家庭是收入分配的主要对象,再分配进一步向弱势群体倾斜。
家庭一直是日本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对象,日本的税收规范及社会保障规范均以家庭收入为核算基础。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日本可分配国民收入总额为 384.18 万亿日元,政府、企业和家庭占第一次分配的比 重 分 别 为 8.9% 、21.65% 和69.45%。其中,薪资总额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高达 91.42%,充分体现了劳动的贡献。在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中,政府、企业和家庭所占比重分别为 3.19%、6.07%和 90.74%,在经济持续低迷状况下,通过越来越提升家庭收入比重来确保家庭总收入的稳定,但政府的负债也随之大幅攀升。
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统计,1976—1997 年的 20 年间,日本家庭占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75%上下的水平。
厚生劳动省家计调查统计显示,以 2009 年单身年收入 300—600 万日元、二人及以上家庭年收入 500—1000 万元作为中等收入标准,中等收入阶层比重为 48.1%,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的比重分别为 17.8%和34.1%。而日本高收入阶层 (最高20%所得家庭)与低收入阶层(最低20%所得家庭)的收入差,则由 1963年的 5.65 倍,降低至 1972 年的仅 4倍,之后略有抬升,2005 年及 2011年分别为 4.31 倍和 4.52 倍。
日本收入再分配的转折点为家庭年收入 550 万日元,550 万日元以上家庭的收入再分配系数为负,以下为正。年收入 800 万日元以上家庭的再分配系数超越 |10%,1000 万日元以上的近 |15%,年收入 350 万日元以下家庭的再分配系数超越 25%,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较大。不只这样,日本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还进一步向弱势家庭倾斜,2010 年再分配中基尼系数 29.3%的改变度中,普通家庭只有 16.9%,而单亲母子家庭的改变度为 28.3%,高龄家庭的改变度达 50%。母子家庭的转移收入主要来自医疗、教育和年金,分别占40.6%、35.3%和 24.1%,而高龄家庭的转移收入主要来自年金和医疗,分别占 64.8%和 20.6%。除此之外,完全依靠社会保障的失业家庭年收入为123 万日元,是普通工薪家庭年收入的 25.5%。
(三)城乡、区域及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行业间与国际接轨。
日本政府很看重城乡、区域及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调节。
2010年全日本总农家数 253 万户,平均每一个农家 3.5—4 个人,农业就业人口251 万。日本是全球农商品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在高额进口关税和农商品价格补贴政策的保护下,收入方面基本达成了城乡一体。
2010 年农民户均收入 466 万日元,其中,农业收入仅为 122 万日元(占 26%),年金等收入 188 万日元,其余均为非农业收入。受集约化程度原因影响,北海道区域户均收入 908 万日元,明显高于其它区域,其乳业经营户收入更是达到了 1198 万日元。
日本的区域收入调节成效也相当好,从第一次收入分配来看,排名前三位的东京都所在的关东 I、关东II、与大阪所在的东海区域最高,分别为 529.8、499 和 529.1 万日元 /户,而南九州、北九州和四国区域却只有 290.9、368.5 和 355.7 万日元,再分配后,则分别提高至 404.1、446.2 和 489.9 万日元,再分配系数达到 38.9%、21.1%和 37.7%。而排名前三区域的再分配系数只有 6.3%、9.0%和 11%,国家在税收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发挥了要紧用途。
2011 年日本全社会员工每年平均收入水平为 401 万日元。从不同行业来看,律师、大夫、飞机驾驶员、与大学教授的每年平均收入在 1100万日元与 1300 万日元之间,会计师及大学讲师等的年收入在 800—900万日元之间。各工业部门中,钢铁厂工人 500 万日元,公交司机 430 万日元,管工 410 万日元,普通工 360万日元,建筑工人 340 万日元。收入较低的为零售、服务行业,超市售货员及其他销售为 320 万日元,出租车司机为 280 万日元,清洗工为 220 万日元。日本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有肯定的可比性。
(四)国企、事业单位及公务员收入公开且透明,收入差距相对合理。
在上世纪 60—7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国企在部分行业中还能发挥肯定用途,伴随民营化改革的越来越深入,日本的国企数目也在迅速降低,现在除邮政部门外,政府只能以持股的方法,通过市场机制在电力等行业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日本对国企、金融机构及事业单位等特殊法人的收入均按明确的法律法规管理,公开透明。
2011 年特殊法人中事务与技术员工的每年平均收入为 677.9 万日元,研究员工的每年平均收入为 1106.6 万日元,社长、理事和监事的每年平均收入分别为 2149.7 万日元、1808.2 万日元和 1477.7 万日元。其电信业国企NTT 的 1.1 万职员每年平均收入为 812.1万日元,13 名高管每年平均收入 4700 万日元。
国家公务员中,局长级年平均收入为 2291.1 万日元;处长级与普通行政员工的每年平均收入分别为 908.2万日元和 632.8 万日元,对特殊法人单位相同级其他人员的收入指数分别为 82.1 和 91.9。从日本的民营大企业 来 看 ,管 理 层 平 均 年 收 入 在4000—5000 万日元,高管收入超越 1亿日元的上市公司须在年报中予以披露。年收入较高的企业中,社长、副社长是职员平均年收入的 5—20 倍。
2、收入分配有关协调与保障机制及用途。
(一)具较完备的社会保障规范,但财政支出过大。
日本的收入再分配主要由年金、医疗及教育等方面的转移支付构成。以年收入 445.1 万日元的普通家庭为例,再分配后所得为 517.9 万亿日元,再分配指数为 116.4。其中年金占转移支付的 22.1%,医疗占 12.6%(见表 1)。日本已基本达成了社保的全覆盖,2010 年底,国民基础年金参加总人数为 6826 万人,其中还有3441 万人参加了厚生年金保险,442万人参加了共济年金。国民基础年金的支取年龄为 65 岁,厚生年金的支取年龄为 60 岁,保险 / 报酬比为14.41%。日本政府统一需要年金的必要加入时间为 25 年,国民基础年金的国库负担率为 50%。
全民医疗保险方面,全国健康保险协会有 1958 万人和 1526.5 户参加保险,健康保险组合有 1557.4 万人和1403.5 户参加,除此之外还有公务员及私立学校教员 452.3 万人及 466.5 万户参保,3876.9 万人(或户) 的农村医疗保险,与 1434.1 万人的高龄者医疗保险等。国民医疗负担中,公费占 37.5%(其中:国库 25.3%、地方 12.1%),保险费占 48.6%(其中,企业 20.3%,职员自己 28.3%),病人自付部分占13.9%。从大体上看,日本 2012 年社会保障的国民负担率为 39.9%,低于英国 45%、德国 53.2%、法国 60.1%的水平,但高于美国 30.3%的国民负担率。
在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状况下,日本国家财政支出重压愈加大,产生了巨额财政赤字。
2012 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数据显示,年度支出总额为90.33 万亿日元,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稳居第一,占 29.2%(假如考虑扣除还债与付息后的支出,则占比高达 38.6%),与 1990 年占政府财政支出 17.5%的比重相比,增长幅度很大。同时,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及债务利息的支出占 24.3%,即 21.94 万亿日元,两者相加就已经占到了全部财政支出的 53.5%。
(二)个人所得税与财产税规范相对健全,但社保已不堪重负。
日本与收入再分配密切有关的主要为所得税和财产税,所得税从根本上体现了对高收入者多课税的目的,可以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与法人税一道成为日本的主流税种。财产税包含房地产税、车船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同样具备较强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在 2012 年 8 月份通过的 《社保—税收一体化改革法案》中,提出将年收入超越 5000 万日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进一步提升至 45%,并自 2013 年开始的 25 年间,对所得税加收 2.1%的附加税。自 2012 年起对法人税加收 10%的附加税 3 年,两项合计可增加 9.7 万亿日元的政府收入。法案中还将遗产税的起征标准由 5000 万日元下调至 3000 万日元,并将最高税率由 50%提升至55%。在进一步加强调节力度的同时,减少政府财政收入重压。
相对较低的社保自负率,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使日本政府出现了紧急的财政赤字。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一路攀升,由 1960 年的0.7 万亿日元,到 1970 年的 3.5 万亿日元,之后又飞速提升至 1980 年的24.8 万 亿 日 元 ,到 2012 年 达 到109.5 万亿日元。社保成本中,年金占比在 50%左右,医疗占比有越来越降低的倾向,其它占比渐渐提升,但总体成本上升明显,政府财政重压日益增大。
日本政府 2012 财政年度预算收入总额为 90.33 万亿日元,其中46.9%,即 42.35 万亿日元为税收收入,其它收入为 3.74 万亿日元,其余为政府新发国债,占 49%。自 1990 年泡沫经济破灭以来,随着着非劳动人口比率的逐年提升,在政府支出越来越上涨的同时,税收收入呈渐渐降低态势,2010 财政年度新发国债初次超越税收收入,财政赤字问题已相当紧急。
为缓解日益增大的政府财政重压,野田政府提出了 3 项重大手段:
一是于 2012 年 8 月份通过了 《社保—税收一体化改革法案》,核心内容是 2014 年将消费税税率由现在的5%,提升至 8%,2015 年 10 月再进一步提升至 10%。来自消费税提升的每年 13.5 万亿日元的收入,将主要用于缓解每年平均 1 万亿日元的政府社保等支出增长。二是从 2013 年度开始将 70—74 岁年龄组的医疗负担比重由现在的 10%,提升至 20%(20—64 及 65—69 岁组段为 30%),75 岁及以上年龄组仍维持 10%不变,预计每年可削减 200 亿日元的政府支出。理由是现在 70—74 岁年龄组医疗平均自己负担的只有 4.7 万日元,而 75 岁及以上年龄组为 7.7万日元,65—69 岁组段为 8.8 万日元。三是下调过去高龄者特别手段中的高额公共年金,2013 年 10 月及2014 年 4 月分别下调 1%,2015 年 4月再下调 0.5%,总计调整幅度为2.5%。该年金自 2000 年度开始已累计超支 7 万亿日元,预计下调完成前还要再超支 2.6 万亿日元。
(三)有效的最低薪资规范与劳资协商业机会制,确立了稳定合作的劳资关系。
日本早在 1959 年就制定和推行了《最低薪资法》,并做了多次修改。
该法规定日本全国各地均要制定最低薪资标准,企业与劳动者订立雇佣合同后,所付薪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薪资标准。并于 2007 年将企业对 1名劳动者未发放达标薪资的罚款,由2 万日元提升至 50 万日元。日本的最低薪资标准使用地方标准与行业准则同时推行的方法,依据国家和各地方最低薪资审议委员会的建议做出决策,并需要行业准则不能低于区域最低标准。
2011 年各区域的最低薪资标准中,东京及附近的神奈川县最高,为 837 和 836 日元 / 小时;冲绳县最低,为 645 日元 / 小时,九州区域除福冈外的 6 个县市均为 646或 647 日元 / 小时;大阪为 786 日元/ 小时,北海道为 705 日元 / 小时。而厚生省劳动局倡导达成的全国最低薪资标准为 800 日元 / 小时。
日本早在 1911 年就颁布了《工厂法》,并在 1946 年和 1949 年先后颁布了《劳资关系调整法》和《工会法》,以规范劳动标准、调停劳动争议、缓和劳资矛盾。此后,又对这类法律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工会法》修改了 17 次,《劳资关系调整法》修改了7 次,而《劳动标准法》则修改了 22次。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颁布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关法律法规,包含《最低薪资法》、《薪资支付保障法》、《劳动安全卫生法》、《职业安定法》、《工伤赔偿保险法》、《雇佣保险法》等。并通过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薪资制、考核评分制、职工持股利益共享制,与设立独立的劳动委员会负责协调与仲裁等方法,较好地处置了企业与职员之间的利益分配,有效解决了劳资矛盾,达成了上世纪 60—70 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集体谈判规范为日本的一大特点,企业与职员通过每年 2—3 月份的“春斗”,达成年度劳资薪资协定。
(四)收入透明化程度高,合法且规范,较好解决了社会矛盾。
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有关法律法规,有效规范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各主要环节,积极解决了可能出现的潜在矛盾与冲突。如其将政府公务员及其他公职职员的收入完全透明化与法律化,既防止了非必须的社会矛盾产生,又为政府与有关企事业之间的职员流动创造了首要条件条件。再如,通过官产学研相结合的方法,努力推进技术革新与职业培训,在越来越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素质的同时,有效增加了劳动者收入,且在上世纪60—70 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同时超越了 GDP 的增长速度,从经济可持续性角度,非常不错地解决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问题。
3、启示与建议。
(一)在强化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同时越来越增涨薪酬,尽快延长退休年限。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维持经济高度稳定成长,达成收入倍增计划的首要条件。为此,国内应充分借鉴日本和德国的进步经验,转变进步观念,努力推行转型策略,加强对企业产品开发的资金和人力支持,看重和强化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确保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的延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通过相应的规范建设,越来越增加劳动者的薪资,提升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勿重蹈德国以外欧元区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忽略劳动生产率提升、一心期望达到较高生活质量,进而致使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覆辙。
日本的经验表明,提升劳动力素质和生产率、增加劳动收入及分配比重是工业化中后期进步阶段的核心任务。将更多的财政盈余投入社会保障而不是扩大中低端产能,从而释放市场需要,是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要紧方法。国内庞大的人口规模更决定了依赖外需和投资是没办法支撑国家整体经济转型的,大比率低端产业及劳动力的存在也将在市场需要、汇率提升等要紧范围,紧急制约沿海区域高档服务业等产业的进步前景,使国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大增。并且,伴随国内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剧,为更好地平衡人口结构变化对收入分配的潜在冲击,保证年金与社保资金来源稳定,需尽快研究并颁布延迟退休年限的政策手段。
(二)确保代际收入的可持续性平衡,从市场化角度做好社保改革。
平衡好代际收入对促进国内消费、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至关要紧。
应牢牢吸取日本的收入分配向老年群体过度倾斜、严重干扰中年轻人群体的消费能力,进而形成老年人储蓄———银行在低息政策下依靠国债收入—政府增发国债—支付老年群体年金的恶性循环等经验教训,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向中年轻人群体倾斜,鼓励革新与消费,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只有做到良性循环才能为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提供持续靠谱的经济和财政支撑。同时,应看到国内将来老龄化进程加快的现实,在通过改革努力减少医疗本钱、强化大病保险规范的基础上,以平均 20%的自负率为医疗保险改革底线,确保老龄化社会到来后,国家和地方财政的稳定与可持续支撑能力。
(三)从长远策略高度重新审视国内的人口政策。
劳动人口比率的拐点不止是日本、欧洲及美国的各种经济泡沫破灭点,更是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财政收入降低与支出持续增加的转折点。基于国内步入老龄化社会、且将面临更严峻的财政支出重压的现实,假如错过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好窗口期,不只将在劳动力提供相对不足、经济增长放缓、国家与地方财政收入明显下滑阶段增加强量的低龄人口培育支出,并与老龄化高峰期出现大范围的重合,还将面临因需要波动而出现大幅萎缩的教育资源紧急不足重压,庞大的人口又使国内不可能像日本那样靠增加国外收益来保持部分赤字,其后果不言而喻。因此,应充分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从人口结构、财富创造、经济成长、收入分配、政府财政收入支出、教育资源、与老年群体社保等多范围的可持续综合策略高度,科学看待与剖析国内目前的人口政策,做出准时有效的调整。■